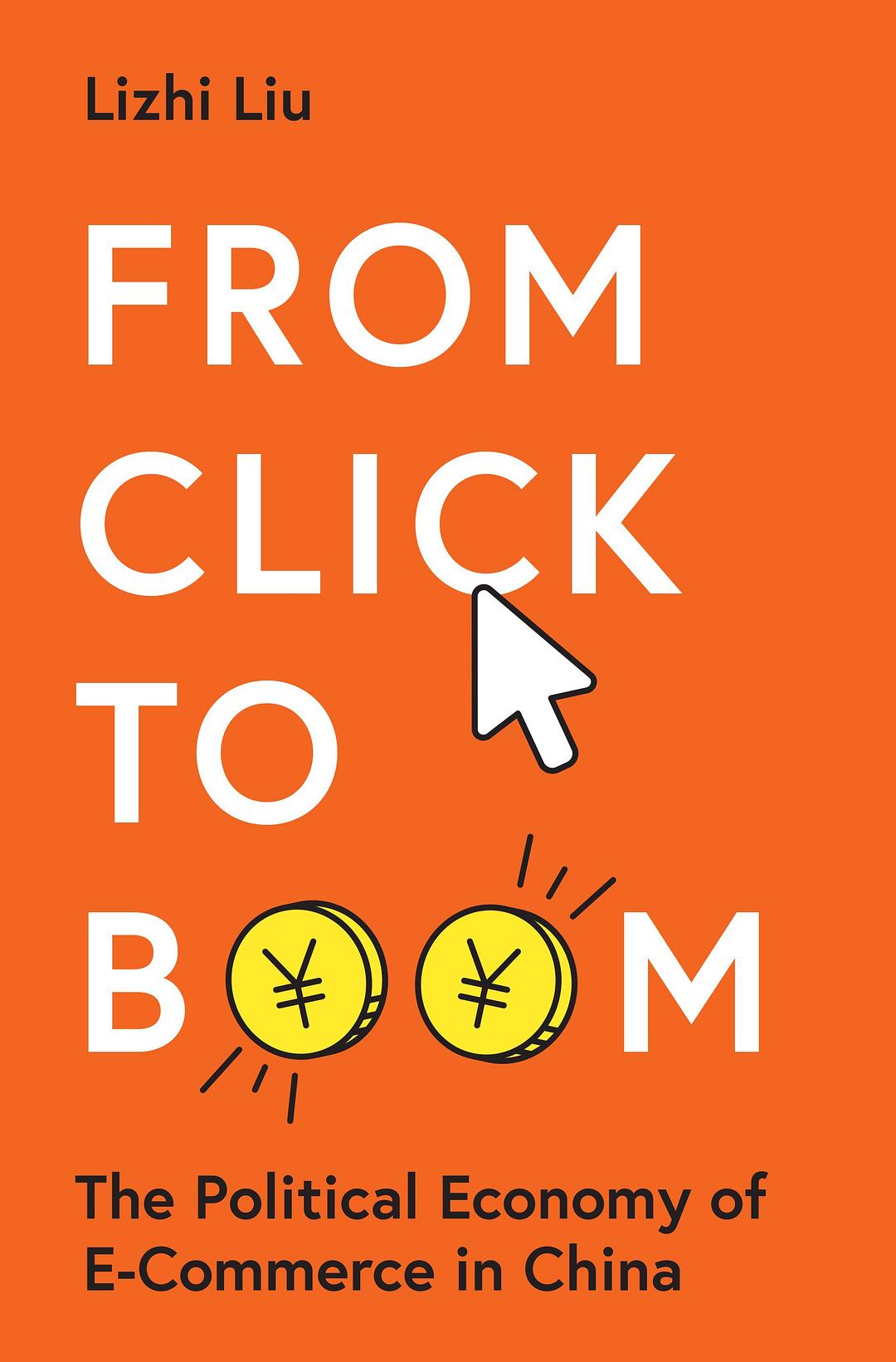
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Lizhi Liu,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4.10,本书已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旗舰店(国内电商平台)上架
美国乔治城大学麦道商学院刘立之助理教授的新作《从点击到繁荣:中国电子商务的政治经济学》(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1]近日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原书娴熟运用多种方法,提出以“建制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概念为核心的框架,一并描述、解释了中国的平台监管、市场建设和经济崛起等领域内若干费解的问题。其中部分章节的早期版本曾以单行论文发表,当时即已引起广泛关注和好评。组织成书后,框架更完整,故事也更圆满。
内容概览
按原书章节的顺序,可以将其主要内容大致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提出和阐释建制外包。按其所述,系指“在法制尚不健全或难以全面执行的情况下,政府通过默许或合同,将部分政经和社会职能外包给以平台企业为代表的‘私有监管中介’(Private Regulatory Intermediaries)。”[2]在过去二十年来国内电子商务平台演进的语境中,这一概念展现了很强的描述力和解释力。电子商务平台不仅是撮合交易的私有中介,还通过建设电子支付、信用体系和争议解决等系列制度——原书对此历程有详细生动的描绘——从而实际承担了私有的建制和监管职能。其间或而默许克制,或而与之合作的政府,得以在无需显著变革其他部分制度的同时,建设起非人格化、规模巨大且嵌入先进技术的市场制度。进而,建制外包不仅描述和解释了平台和政府间如此前所罕见、各据其位而又必然充满张力与动态的关系,也间接纳入了个体用户和企业等其他相关的主体。建立于其上的框架不仅可以用于电子商务平台,也有可能推及更广的场景。原书其他部分的理论和实证,相当程度上是对这一框架的不同角度展开。
二是主要通过淘宝和易趣(eBay)竞争的案例研究,在为未必熟悉中国电子商务的国际读者解释必要的背景信息的同时,微观地展示建制何以外包,以及私有监管中介何以崛起的历时过程。这个过程显然无法用一两句话尽数概括。不过,如果一定要简化地叙事,二十一世纪初时一度在世界范围,当然也包括国内,风光无限的易趣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了其发源地美国已经具备的基础深厚的市场制度,没有必要再为买家付款信用、卖家发货信用和双方争议解决等“小”问题投入太多。而在当时的国内,这些制度都还在草创阶段,电子商务平台需要自己动手解决这些问题。淘宝用非常本土化、“接地气”的方式供给了这些制度。支付宝、信用等级、大众评审、阿里旺旺……这些名字今日依然耳熟能详。相比之下,易趣在本土化的制度供给方面就要迟缓得多。原书通过对比并排除其他许多当时看来淘宝相比易趣在竞争方面的劣势,论证了建制因素能够有力地解释为何是淘宝最终胜出。当然,绝不能完全忽视政府的作用(参见71页)。
三是通过综合质性和定量的实证方法,探讨电子商务平台兴起对政治系统内权力配置,特别是央地权力格局的影响。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有两方面。其一是平台兴起如何影响各类商户,特别是中小型企业以及规模更小、更为零散的个体商户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既包括相对正式的产业扶持、税收缴纳、执法检查等关系,也包括相对非正式的交往沟通和关系维护。借助精心设计校准、提高数据效力的全国调查数据,以及更加独特难得、可与前述数据匹配的淘宝内部的微观数据,再用构造对照组的思路开展因果识别,原书发现平台兴起确实削弱了商户和当地政府的关系。遭到削弱的不仅包括正式的关系,也包括非正式的关系。换言之,各类商户更加依赖于外包至平台的交易和信用建制,而在产业扶持、税收缴纳等方面更少依赖于地方政府,也更难为地方政府所管辖。各类商户与地方政府的交往沟通和关系维护频率也有减少。原书用相当数量的访谈材料,包括对商户和地方政府的访谈材料补强了这些结论。相应章节的开篇还引了受访者的一句俏皮话:“不管就是最大的扶持”(83页)。至今,每当涉及新兴领域是否需要制定新法律或新政策的问题,这句话依然有着很高的出镜率。其二则在前述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分析权力格局的移转。地方政府的权力或有削弱,商户转向依赖平台,同时意味着权力向平台的流散。与此同时,如原书所论,中央政府仍旧对平台等私有监管中介保有“终极的控制”(45-46页)。两相比照,平台崛起重塑了中央和地方间的权力格局。中央,而非地理上更临近的地方,对各类商户所依赖的平台建制握有终极的、也更直接的控制。引申而言,中央和地方间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当然也是多个学科长期以来密切关注的问题——亦有可能因此倒转。这一深刻的结论在国内相邻的学科中已经引起丰富的回响[3]。笔者之前也曾不止一次引述此处结论[4]。
四是通过至今在平台研究中依旧可称珍稀的随机对照试验方法,研究平台下乡对农村脱贫这一治理目标的贡献。概言之,通过与作为研究对象的平台合作,可以通过随机对照试验这一因果识别的“金标准”,科学地、定量地、精确地估计平台下乡如何通过不同的机制渠道改进农村居民的福利。这件事显然并不容易。原书也专门论及如何在争取实地实验机会的同时,坚守和保障学术研究的客观中立,令人感佩(134页)。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对实地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来说,最终清澈如水、令人信服的估计结果,背后总是研究者一力承担了大量纷繁的、日常的工作。通读原书可隐隐想见诸多有趣的细节,不再赘述。这里只概览三方面的主要结果。一是基于随机对照试验可以精确估计电商下乡对单个村庄的福利效应,平均而言约为每个村庄十八万元(154页)。参加电商下乡项目的总共有三千个村庄,可知总福利效应达约五亿四千万元(第155页)。[5]小小的电商有显著的影响。二是电商下乡的福利效应的作用渠道值得进一步考察。简言之,电商下乡既有可能通过降低电商平台触达成本、刺激电商平台消费的方式提高村民福利,也有可能通过降低电商平台创业成本、刺激农村电商创业实践来产生脱贫效果。前者固然可喜,后者则更加符合农村脱贫的治理目标。对随机对照试验结果的细致分析发现,电商下乡似乎更多地是“授之以鱼”而非“授之以渔”。为了区分两种不同的作用渠道,原书做了很多细致的实证分析。应该说,如果不是基于这些细致的分析,一般无法得到这种对实践政策制定极有意义,但又很难通过定性方法、其他定量方法乃至其他识别无法得到的结论。三是电商下乡福利效果在个体层面的异质性。直观而言,既然电商下乡提振福利的渠道更多是通过刺激消费,而非促进创业,相比需要通过创业脱贫的个体,更有能力消费的个体享受了更多的福利效应。于是,一方面可以说电商下乡具备整体上缩减城乡差距的福利效应;另一方面也可以说电商下乡可能延续,甚或增加了村庄内部个体间的数字鸿沟。恰似前文所述,不仅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思维中的前见和定势,也是非细致分析不可得的结论。
五是在叙述并尝试解释2019年来国内平台监管的收放起伏的同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业已建成的概念与框架。2019-2024年,对任何一位对电子商务和平台监管感兴趣的研究者来说,都可谓花样纷呈、百感交集的五年。不妨简单列举各时段内最令人深刻的表述。从2019年及之前出现频率更高的包容审慎监管——原书亦有专门的探讨(74-76页),再到其中一段时间内相对突出的“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6]其后则有至今时时出现的“常态式监管”,[7]以及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加强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8]。其间学术和政策思潮的同向起落,犹然历历在目、清晰可见。[9]原书以编年形式列举了从“过度反应”(168页)到“凛冬将至”(171页)再到“回归”(175页)的大事件(172-173页),主要将其视为对一系列现实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回应。综之,可视为一部平台监管的精炼扼要、外部视角的极简史。建制外包还在继续,且愈发与监管纠连(176页)。
概念与方法
原书在题目选择、概念提出、方法选用和跨学科对话方面亮点迭出。笔者相信无论是学术上的小同行、大同行还是大众读者,都能欣赏其中的一个或者多个侧面,并且有所收获。在此,只概述感受较深且上文未及的五点。
一是其间的发现和分析意义广泛,足够新颖且足够重要。即使读者并不是处于本书所跨越的几个学科的小同行或大同行,亦然如此。为什么?因为研究的是过去二十年发生在每个人的电脑和手机当中的事情——甚至一定程度上还解释了为什么二十年后每个人都至少有一部手机。交互硬件和媒介软件的变迁,无疑都是中国电子商务平台的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换言之,虽然原书题目中的“政治经济学”似乎暗示了一个相对宏观的视角,但无论是从研究视角、材料范围、数据粒度、研究结论还是研究意义中的任何一个角度来看,原书都和二十年里十四亿人的日常生活变迁息息相关。譬如,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对中国和美国平台崛起的比较,不仅落在电子商务等各类平台的责任承担与豁免等宏观制度的层面(189-190页),还体现在商户信用展示界面是不是采取了“(金色)皇冠”等本土化元素等微观设计的层面(73页)。因此,既有相对宏观层面的“从点击到繁荣”,也有微观生活层面的“从点击到爆发”。或者说,为什么只要解锁屏幕,轻轻点击几下,就会有千万上亿种商品和内容爆炸性地呈现在眼前?
二是原书核心概念和框架,特别是上文着重介绍的建制外包,不仅具备很强的描述力和解释力,还有相当的包容力和可扩展性。这些优点可以从两个维度上得到佐证。不仅解释了过去二十年间电商平台的崛起,也能包容过去五年间监管一定程度的“无常”,这是一个维度;不仅解释了平台崛起和政府监管间复杂的互动模式,还解释了平台建制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这是一个更宏大的维度。如果再作引申,对于今天国内热议的营商环境建设问题,以及正在制定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基于建制外包的框架或许都有相当现实的意义。不妨只谈最直观的一点。一直以来,对“民营经济”这一表述,都有宜调整为“民有经济”的呼吁。建制外包二十年来波澜壮阔,所建之制主要来自同属民营经济的平台企业。进而,或可探索“民建经济”这一概念。特别是在电子商务中,作为“营”和“有”的基础的制度,包括交易和信用制度,相当程度要归功于同属民营经济的电商平台。换言之,支持物权平等保护不仅有其他许多重要的原因,还因为如果没有平台经济,一定程度上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熟悉的“制”和“权”。
三是原书方法多元。恰如其封底推荐语所述——每一句推荐语都所言不虚,这一句又实在尤其贴切——“它[原书]结合的多重研究方法处于最前沿,为研究领域树立了新的标准。”[10]换句话说,原书不同章节综采的方法,让人颇有“十八般武艺”目不暇接的感觉。从质性方法到随机对照试验,再到简约式估计和结构式估计,当前相关学科中常用的方法,都在贴近其问题情景的章节中出现过。如果一定要开玩笑地苛求,唯一还没有出场的方法,大概就是有策略互动(博弈论)的结构式估计。特别是,相比国内平台监管领域现有的实证研究,随机对照试验和结构式估计的引入应当属于相当的突破,理应成为新的标准。如果不能推动补充这两类识别方法,平台监管的许多问题不太可能做得非常深入。
四是结论丰富入微。这是原书两方面要素交互作用的自然结果。一方面是数据和材料的丰富程度。透过显然只在书中体现了原始数据和材料的很小一部分的微观数据和访谈记录,读者容易感受到原书远超一般研究的厚重程度;另一方面则是多元方法与厚重材料的交互作用,用两个笔者随口说来的数字就是,假如用五种方法作用于五倍的材料,最后的结语可能将是二十五倍地丰富。故此,原书不仅正文部分值得阅读,其一百多页的附录部分也不妨一阅。对于没有那么重要的问题,我们不妨观其大略,知晓主线结论即可;对于过去二十年间的平台崛起、建制外包和经济发展这样重要的问题,哪些假设在经过详实的检验之后得到了验证或排除,哪些结论在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下屹立不倒或则摇摇欲坠,异质性分析是否揭示了理论与现实交界处折射的多路光影,等等,都值得进一步的研究。上文提及电商下乡的作用渠道和个体效应的异质性,就是典例之一。
五是激发跨学科的共鸣。以笔者目力所及,原书方法和结论可以相当自然地和经济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商学、法学乃至其他更多国际的和本土的学科形成对话。就此,不妨仅以笔者所在的法学(甚至可以进一步限缩至行政法学)为例,以建制外包和私有监管中介为核心的框架,可以相当自然地与国内学界近来热议的“私权力”“非法兴起”“公私合作性行政”“网络平台公共性”“具体媒介具体管理”“区分(经济、社会、国际、政治)领域监管”和“私人承担公共治理义务”等众多概念形成对话。[11]或者说,不仅共享相似的研究背景和问题意识,彼此亦有可能以建设性的方式磋磨互补。如前所述,原书在方法和结论上都可以对法学研究形成显著的增益。反之,无论是法学,还是其他同样关注平台监管的国际或本土学科,也足以为延伸原书探讨提供有益的语境和脉络。
延伸的探讨
原书为继续深化相关的研究打开了广阔空间。即使只以最朴实的方法期待,一旦已经成功地将如此丰富的概念、方法、学科、时段和地域按学术界认可的方式实现交叉,经纬交织的各个连接点就都可能代表潜在的新方向。可以期许未来出现更多推进的工作。篇幅所限,只就建制外包稍作五点延伸的探讨。
一是原书似乎在其绝大部分论述中,假设平台监管的逻辑,特别是政治、政策和理论等层面的逻辑具有较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或者说,除了主要由第六章精炼叙述并尝试解释的五年,偶然、失误、无意识乃至不理性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不是电子商务平台监管及其政治经济学叙事的主角。或者说,对于平台监管上显著的反复或摇摆,如果没有其他质性或数字上的证据足以区分二者,则在叙事上更倾向于进退有据、有时过度的收与放。各方仍然是在理性地选择,只是信念未必准确(169-171页)。[12]对此,相信至少还有三类研究可以形成补充。其一是监管学习。与电子商务和其他平台交互的过程,也是监管机关不断学习的过程,其知识信念和行动逻辑在这一过程也在不断更新,需要在历时的视角中理解。[13]其二是平台监管中常常成对出现,口语色彩浓烈但已基本学理化的一对表述——不同部门间的监管“碎片化”(有时进而称为“九龙治水”)[14]和不同位阶法律间的“效力倒挂”。[15]值得补充的是,原书实际已在相当程度上揭示并解释了中央和地方在平台监管知识、理念、立场、工具和力度等方面的相通和歧异,也提及了滴滴在焦点案件中“混杂的信号”(171页、285页)。其三与一二密切相关,平台监管亟待采取更加内部、也更加过程性,从而对偶然等因素更加开放的视角。当然,这样的苛求常常实践上不可行或不可能。关键的材料得不到,关键的人访谈不到,这些困难都客观存在,远不在设法开展实地实验之下。不过,始终是值得追求的研究目标。
二是原书对平台及其商户、用户在建制方面的自主性(Autonomy)展开了专门研究。总体而言,平台及其商户、用户在建制过程中更多只在技术和商业方面发挥作用,在其他方面则相对被动、无意识。恰如建制外包这一概念所暗示,发包方显然有更多的主动地位,接包的则是被动一方;亦如其第三章专门论及:电子商务平台的崛起并没有转化为更多的政治参与。平台是否确实缺乏这方面的自主和意识,也许是一个时间上值得再做一些知识考古、空间上亦可增加理论和实践比较的话题。不妨随意交织一些时空之间的经纬。美国法学界近年来有一对颇为热门、影响广泛的概念,谓之监管创业(Regulatory entrepreneurship)和规范创业(Norm entrepreneurship)。[16]简言之,此类创业的目标就是建制或变革制度,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优步等出行平台。比照而论,如果在监管侧的叙事中增加更多的偶然性,而在平台侧的叙事中增加更多的自主性,相信也可以形成另一种同样相当有竞争力的框架。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法学等相邻学科已有一些这样的研究,如颇有影响的“‘众创’式制度变革。”[17]
三是对政府与平台的互动关系稍作延伸之后,继续立足建制外包这一概念,或可延伸探讨建制的可外包性问题。[18]一言蔽之,特别对政府来说:可以外包还是不可外包,可以外包的前提下要不要主动发包或者容忍外包?这些都是问题。沿用原书的理论框架,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可外包性的问题。其一,沿用以交易成本为核心的制度经济学领域经典的“大教堂”(Cathedral)一文——国内法学常称为“卡-梅框架”——是否可以同样主要从交易成本出发,分出可外包性的三个地带?[19]也就是,有的建制外包可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协议方式自由地安排和流转,有的建制外包更多地是摊派或倒逼,还有的建制则是不可外包的“红线”。其二,如果将问题拓展到动态的情形,建制外包的进程是否可逆,是有可能收放自如、进退裕如(17页、264页),还是有可能像其他的建制方式一样“一去不复返”(29页)?甚至是否有可能随着外包的发展,导致俘获进而“施加政治影响”的现象?(169页)对于建制外包是否可能逆转或收回,相关各方都处在一个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需要充分确保掌握收放进退的权力,对外包是否可逆以及相应的可外包性的判断也许相当重要。其三,与一二密切相关。原书似颇受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研究的影响。不仅作为理论资源之一(36页),也提及了“财富的逆转”等表述(81页)。循此,不妨回归阿西莫格鲁早期一项探讨制度效率重要性和低效制度之成因文章。为什么低效的制度如此普遍,且随时间推移依然牢固?相当简略且不严格地说,因为在政治上终究难以做出可信的承诺,与建制相关的“交易”成本——当然也包括外包和收回外包的“交易”——常常有可能是无穷大,也就是不存在政治意义上的科斯定理(Political Coase theorem)。[20]这一观察和建制外包的(不)可逆性与(不)可接受也许存在密切的关系。从而与原书结语中的表述呼应:要想拥有“足够强而又不太强”的政府,总是困难的(193页)。
四是如果对政府和平台的关系从另一角度延伸,恰如原书在结语部分所提及,“政府和商业的模糊边界”(181页),可以从边界的角度设问。或者说,政府权力的边界、平台权利的边界和平台权力(可比较前述私权力等概念)的边界都在趋于模糊。即使将平台置于相对被动且不自觉的角度加以审视,只要其事实上承担了建制职能,并拥有一定的权力,就可以探讨其权力的所至边界及其在权力体系中的定位问题。进言之,如果用政治学探讨里常用的“条”“块”概念来表述,平台既不属于条,也不属于块,但又可以影响条块之间的相对关系,并在条块之中占据一个相当独特的生态位。[21]其边界与定位始终是个饶有趣味的问题。不妨仿照原书结语部分,亦与大洋彼岸稍作比较。在研究美国大型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审查和其他权力时,凯特·科洛尼科(Kate Klonick)直称平台为新统治者(New Governor)。[22]与此同时,这一表述总是让人联想其是否又意指新的州长,或者说平台是否新兴的“州”,是否合众当中的新的“众”。
最后,不妨以开始超出学理探讨、更加强调实践决断的方式,在原书结尾处对“有所不为”(193页)再行延展。如前所述,“常态化监管”是在平台监管领域至今依然不时出现的概念。既然有“常态”和“常态化”,那就不仅暗示了“非常态”,也暗示了“常态”和“非常态”之间的转换。由此,完整的理论不仅应该是能够解释常态化,也可以解释非常态化,还能够解释常态化和非常态化间或许可逆,或许不可逆的转化。无论我们是在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dt)的意义上使用非常态,还是在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意义上使用非常态,相应的理论总是难以脱离未必尊重理性的、实践中的决断,也必然蕴涵着令人惊骇甚至无言的断裂。当然,也许存在其他的理论化非常态这一概念的方式。然而,如果坚持前述很少出现在平台监管研究的理论进路,这就回到了本节开头的一段:尽管学术的生产规范要求追求并展示尽可能的融贯与完整,但过度的融贯与完整,也可能在充满偶然、变数甚或荒诞的历史演进中,或者在“一条向前的不确定道路”上(191页),赋予我们过度的信心。
结语
上文首先概述原书的主要内容,然后列举个人阅读观感中最明显的一些亮点,再提出一些延伸的探讨。显然,还有太多精彩的内容没有来得及提到,许多评述相信也是阅读不够细致之下的片面之论。相信阅读原书将会带来不可替代的精彩体验。作为多年前就在关注修改后成为本书随机对照试验一章的单行论文——当时还只是工作论文——的忠实读者,也很感谢正是那篇论文成为有幸与原书作者结识的契机。坚信原书将成为平台监管领域引起学术繁荣的一次点击,成为平台监管领域一个引人注目的“爆点”。
——————————
注释:
[1] 本书书名中译参见刘立之:《新书首发 | 从点击到繁荣:中国电子商务的政治经济学》,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公众号,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1PDDb1DGoELPMgU9NinuA,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2日。下文凡从其中引用书名、概念及相关章节语句,均不再赘注。
[2] 参见Liu, Lizhi. From Click to Bo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Commerce in Chin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4: pp. 13. 以下凡引原书,均仅夹注页码。
[3] 例如,参见向静林、艾云:《数字社会发展与中国政府治理新模式》,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1期:第4-23页。
[4] 例如,参见朱悦:《从法的实验到实验的法:A/B实验如何变革互联网治理 》,载《网络信息法学研究》2021年第2辑:第55–82页和第294-295页。
[5] 此处的福利计算结果或有换算上的小误。结合其他相关数字,其间“54亿人民币”(“5.4 Billion”)疑为“5.4亿人民币”(即0.54 Billion)。
[6] 参见中国政府网链接:https://www.gov.cn/xinwen/2021-03/15/content_5593154.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2日。
[7] 参见中国政府网链接: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9/content_5688016.htm,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2日。
[8] 参见新华网链接: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1212/f47e778630ec4ff6b51c99d55cef6f43/c.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4年12月22日。
[9] 例如,分别参见刘权:《数字经济视域下包容审慎监管的法治逻辑》,载《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第37-51页;郗戈:《“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4-18页和第199页和罗文:《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载《求是》2024年第17期:第41-46页。
[10] 参见前注1。
[11] 例如,分别参见周辉:《变革与选择:私权力视角下的网络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胡凌:《“非法兴起”:理解中国互联网演进的一个视角》,载《文化纵横》2016年第5期:第120-125页;章志远:《迈向公私合作型行政法》,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37-153页;刘权: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第42-56页;左亦鲁:《具体媒介具体管理——中国媒介内容管理模式初探》,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2期:第11页和第191–206页;丁晓东:《论超大型互联网平台的法律规制》,载《法律科学》2025年第1期:第94–108页;孔祥稳:《私人承担公共治理义务的正当性及其界限》,未刊稿,等等。
[12] 特别有趣的也许是原书第171页的举例。也许许久我们才能清楚(尽管这确实是个因果性的问题,但也许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因果识别方法能解决的):究竟是未能预见所以批评,还是已经预见所以批评。
[13] 例如,参见蔡泽洲、薛澜:《不确定性下新兴产业监管的组织学习——以中国电商平台监管为例》,载《管理世界》2024年第12期:第147-170页。
[14] 例如,参见周汉华:《论互联网法》,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20–37页和Zhang, Angela Huyue. High Wire: How China Regulates Big Tech and Governs Its Econom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4.
[15] 例如,参见Miao, Weishan, Min Jiang, and Yunxia Pang. "Historicizing Internet Regulation in China: A Meta-Analysis of Chinese Internet Policies (1994–201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5 (2021): 24.
[16] 有关监管创业和规范创业,分别参见Pollman, Elizabeth, and Jordan Barry. “Regulatory Entrepreneurship.”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90:3 (2017): 383-448和Waldman, Ari Ezra. “Privacy, Practice, and Performance.” California Law Review 110 (2022): 1221-1280.
[17] 例如,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建设中的“众创”式制度变革——基于“网约车”合法化进程的法理学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第75-97页和第205-206页。
[18] 值得补充的是,原书专设“外包的界限”一节(第48-49页),主要从社会效率的角度探讨是否宜于外包的问题。
[19] 参见Calabresi, Guido, and A. Douglas Melamed. "Property Rules, Liability Rules, and Inalienability: 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 Modern Understandings of Liberty and Property. Routledge, 2013. 139-178.
[20] 参见Acemoglu, Daron. “Why Not a Political Coase Theorem? Social Conflict, Commitment, and Politic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1.4 (2003): 620-652.
[21] 参见前注3。
[22] 参见Klonick, Kate. “The New Governors: The People, Rules, and Processes Governing Online Speech.” Harvard Law Review 131 (2018): 1598-1670.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0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
京ICP备11000001号